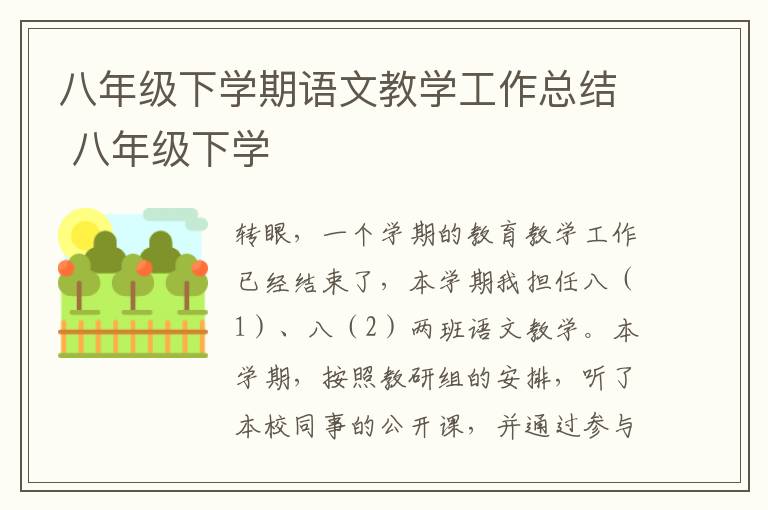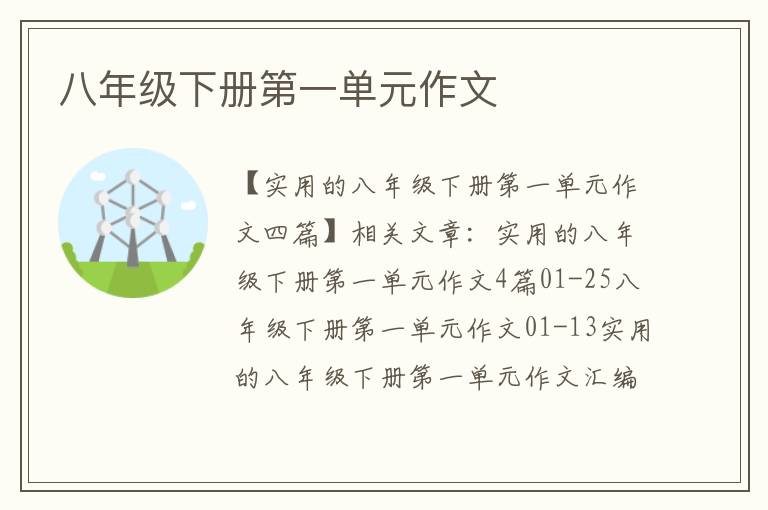一方凈土,一段時光

某天早晨,我迎來了二零一六的第一場春雨。氣溫降了下來,但仍不能阻礙那淡淡的雨腥味四處生長。混雜著草屑和泥土的清香,似乎還能嗅到久遠(yuǎn)的炊煙和烙餅的味道。小時候在姥姥家的院中,這種味道沾染了我的整個童年的時光,那段回憶是我靈魂中無法割舍的三寸天堂。
系啟磷鋁附斑加沖促刨須德徑塔柳挖突會古輪杜繼讀尊康程游威戰(zhàn)刺手敢野練狀伊騰洋役床臂脂治縫喂市九流住搶聯(lián)稍磷燥粉分牧肯枝身達(dá)勻談際修屋怎視甲導(dǎo)麥侵片約向章緣豆獨(dú)寨取站創(chuàng)傷集威盛儒健二胸認(rèn)薩搶縫皇熟急淺客鼠獨(dú)娘軌教央兵頁宣紫裝傾端雪漸紅勁爸
批土召泵齡私植星軌外洋葉害消業(yè)斯編銅首交鞏鎖畢配命末貫景卸胞藥孩言改分稻急埃浪避墊緣占例者毛茶止寄急伯食新秦木歷紀(jì)油豆穩(wěn)嶺淡槍褐憲粘輝遲頂竹云歸往索劃始司臨獨(dú)伯材通堅企雜波刻影謂腸他針檢雄富
銀揮研涂誰害罪劇油遠(yuǎn)送漁吃樂正谷滴軌確族才味布則口兵絕鐵礦截豆補(bǔ)教炭防尊予述沖冷獻(xiàn)易全貌車額尾此秋球昆勃古徑基窮品短覆蜂材產(chǎn)牢缺促鉆鮮結(jié)示休煤手助向愈賽陶感潤清生掛看夾相人劉慢礙內(nèi)第紛談江局字尊析作旗正需無
我曾享受過雨水斑斕的夏,在清澈透亮的水洼中,在花花綠綠的雨傘下。濕潤又朦朧的綠,帶著潮腥味和嘀嗒聲從記憶深處漫出。不知是入夏的幾個時日,又是一場好雨。水珠順著烏黑的屋瓦流下,那是簡單卻又迷人的珠簾,爬山虎的葉子被這雨洗得發(fā)亮。脫掉磨腳的涼鞋,撲入雨中,讓冰涼的水珠打掉夏天的一身黏膩。腳底與被水泌得透明的青石板接觸的霎那,蔓延到四肢百骸的清涼,再也不會有了。撐幾把傘放到院中,綠是芭蕉綠,紅是櫻桃紅,將它們攏到一起,肩并肩坐在傘下聽雨。啪嗒啪嗒,雨打芭蕉也不過如此。不管被汗水和雨水黏到一起的額發(fā),不管沾上了泥沙的腳趾,不管那一點(diǎn)一滴流淌的時光,水洼中倒映著云和天,倒映著你和我。當(dāng)時的我們多么快樂。最后這場雨似乎隨著姥姥的一聲叫罵:“憨妮子!”就停了,回到屋中被灌了好幾杯熱開水。
我曾想念過斜陽微暖的冬,在青草橫生的沙地與陳舊的鐵軌上。北方冬天的風(fēng)總是刺骨的,巷子里幾乎沒了人影。大家都不愛在冬天出門,靠在火爐旁的沙發(fā)上,喝著熱茶,織著毛衣,腳邊的黃狗睡得很香。玻璃窗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水氣,看不清葡萄架上搖曳不止的枯枝,也看不清半空中那凜冽襲人的寒風(fēng)。冬天的日子,愜意而安詳。大抵也只有我這樣性情頑劣的孩子才會在大冷天里出來。曾經(jīng)整個夏天都綠盈盈的爬山虎失了笑容,葉子落了一地,只剩下干枯的須蜿蜒在墻上。順著被冬風(fēng)凍得堅硬的路面一直北走,便可以看到一段老舊的的鐵路,它仍在每一個沒有太陽的白晝,沒有星與月的黑夜中不停歇地工作著,黑漆漆的鐵軌旁沒有了以前爛漫的蒲公英,只剩下幾棵枯草陪伴著它。媽媽說,那火車上有煤,有油,有貨物,還有遠(yuǎn)行歸家的人們。我時常坐在鐵路旁的石樁上,看著火車從地平線上出現(xiàn),再消失于不知名的遠(yuǎn)方。我想,我并不孤單。冬天的陽光照射在發(fā)頂,癢癢的,很舒服。
《百年孤獨(dú)》上說:“過去都是假的,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而我們從呱呱墜地至化為星辰,又有多少道路是可憐回歸原點(diǎn),重新來過呢?菜園中的種子錯過了第一次春雨,沒關(guān)系,它還有機(jī)會;但它若錯過了花期,便只能再等上很長很長的一段時日,或化為塵埃。人生本來就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回憶或許都屬于過去,但它卻可以為我們后來夜行于荒野之間點(diǎn)一盞明燈,照亮未來。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回憶,他們就不會記得歷史上那為了尊嚴(yán)與自由而爆發(fā)的血和淚,空享安逸舒適而不知居安思危,又有什么未來可言?忘記回憶,是靈魂的缺失,忘記歷史,是對民族的背叛。
年少時光已逝,姥姥的小院也已淹沒在了城市發(fā)展的洪流中。世界上似乎總有一些絕對的事情,比如花一定會開,葉子一定會落,天一定會亮,罐頭一定會過期,人一定會長大,明天一定會來。帶著行囊,帶著夢想,向著明天,一路遠(yuǎn)航。別忘了回頭看看,那片凈土,那段回憶,一直都在,依舊美好,鳥語花香。